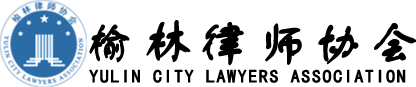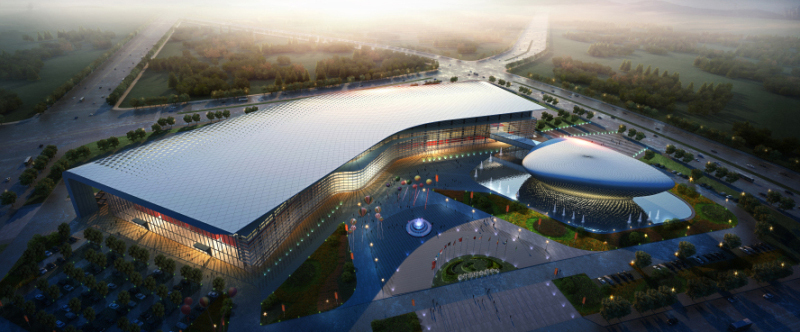发布时间:2017-08-27 10:23:40 作者:陈震 信息来源: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
《浅析被害人谅解在刑事诉讼中价值》
---第九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论文征文一等奖
摘要:一直以来刑事诉讼最大问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为此刑诉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赋予许多权利,但作为犯罪最直接的受害者被害人权利如何保障无疑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聚焦在被害人方面。把握被害人谅解的价值, 使其在量刑中发挥作用,可更好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缓和犯罪行为对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以此体现其价值。
关键词:被害人谅解 量刑 和谐
引 言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传入,被害人谅解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也更多更深入,并被应用到实践之中。从司法适用的结果来看被害人谅解确有显著的社会关系修复作用。被害人谅解不断更新着人们对它的社会意义的认识,不断改变人们的唯刑罚论的观念,学者们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是从浅到深。但每一种理论学说都不是一下子能被人接受,都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完善,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也不例外,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一、被害人、谅解、以及被害人谅解的概念;
理解被害人谅解的内涵,首先来解读“被害人”。现代意义上的被害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指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单位,广义上指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人、单位,以及与他们有利害关系的近亲属。但国家不属于被害人,因为国家享有刑罚权,对犯罪人谅解完全可以通过特赦或大赦等方式量刑。因此,刑事被害人是指因犯罪行为所遭受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并具有控告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谅解”不同于平时理解为情感、道德上的谅解,法律意义上的谅解具有行为性,谅解行为人改变对犯罪人的敌意态度,通过要求或默示对加害人的减轻、从轻或免除刑罚处罚的行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来将真实意思表达出来 。
综上,我认为被害人谅解应定义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并具有控告权利的自然人和单位,通过对犯罪事实进行权衡,基于真实的意思向司法机关明确要求或默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减轻、从轻或免除刑罚的司法行为。
二、被害人谅解作为定罪、量刑情节理论发展过程;
关于刑罚根据的理论主要有等害报复、刑罚功利主义、以及现在广泛被采纳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每种理论学说各有侧重点和其社会意义。
1、等害报复理论中,适用刑罚只关注犯罪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而不考虑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换句话说,等害报复理论中适用刑罚时不论犯罪嫌疑人是谁,只要犯罪造成的客观结果相同,施加的刑罚就相同,类似古代同态复仇。而就量刑来说,遇到某一具体案件,对犯罪人处以何种刑罚,要兼顾犯罪人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和犯罪行为具体造成的损害结果。在等害报复理论中,定罪与量刑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只存在定罪这一个环节,而被害人谅解是一个罪后情节,无论谅解不谅解,犯罪行为早已结束,都无法改变犯罪行为已造成的客观损害的事实,所以在此理论中被害人谅解不能被纳入到量刑情节当中。
2、刑罚功利论主张刑罚的功利性,刑罚的轻重、刑罚的方式都要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为目的,所以量刑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犯罪人本身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3、恢复性司法理念中,主张当事人积极地交流,让损害在当事人内部得到消弥。就被害人来讲,使其在精神和物质上得到赔偿;就犯罪人来讲,让其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和痛苦,进而悔过自新。从中看出,恢复性司法将目光更多地放在了被害人身上,尊重和保障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所以恢复性司法以双方当事人和解为主要特征,注重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且被害人可自主决定要不要原谅犯罪人,所以将其引入量刑情节是理性的选择。
三、被害人谅解引入量刑的所存在的问题;
被害人谅解应否引入量刑情节,学界也是众说纷纭。由王瑞君教授《刑事被害人谅解不应成为酌定量刑情节》中便鲜明地指出被害人谅解引入量刑情节种种的不合理之处。其中报应刑罚理论中,被害人谅解要具备量刑作用,或者能体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或者能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然而被害人谅解属于罪后情节,此时犯罪行为已经完成,被害人谅解或不谅解都无法改变犯罪行为造成的客观损害结果。除此之外,有时被害人做出了谅解并不意味着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已经降低。
司法实践当中,被害人谅解犯罪人基本存在这三种情况:一种是被告人真正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恶性,十分真诚地向被害人或其家属忏悔;其二被害人因犯罪人的高额赔偿而做出谅解;其三案件发生在亲属之间,危害性程度较小,或者是轻微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第一种情况中,犯罪人真诚悔罪,其人身危险性降低,那么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就降低了,此时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就是合理的。但第二种、第三种情形中,通过赔偿达成和解协议,很难评估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否降低,也就无法判断是否能够对犯罪人减刑,有些被告人甚至认为钱都赔给你了,也就不拖欠你的了,不存在对不起被害人,没有了良心上的愧疚。此时,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就会存在一定问题,富人犯罪永远被谅解。所以对于被害人谅解是否作为量刑情节一定要慎重,否则会适得其反。
四、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参与人,我们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关系体系的稳定,更要让被害人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得到补偿。将被害人谅解纳入量刑情节体系,使被害人不再游离于刑事诉讼的边缘地带,而是真正参与到刑事诉讼中,这既是基于被害人利益的考量,也是为被告人悔过自新的考虑,是人本精神的体现。结合理论与实践就被害人谅解引入量刑情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其具体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
1、恢复性理论,从恢复性理论上来讲,刑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犯罪扰乱社会秩序,当课以刑罚来惩戒;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被害人的健康权、财产权甚至生命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做出相应的道歉和赔偿使被害人的正当利益得以恢复或者尽量得到弥补。
2、司法效率理论,从司法效率理论上来看,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就是国家对一个人发动的一场战争,国家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复杂案件还需要补充侦查、检察院抗诉、二审等法律程序,漫长的司法程序往往使得被害人的权益长期得不到恢复,而且司法诉讼所耗时间又会对被害人构成“二次伤害”。在实务中有许多不应当抗诉的案件由于被害人及其家属“折腾”检察院,致使检察院不得不向法院提出抗诉。而通过被告人积极赔偿悔过以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减轻犯罪人的刑罚,将有效提高诉讼效率,降低抗诉率,节约司法资源。
3、被害人主体地位理论,从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性理论上来看,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后果是由社会人来承担,犯罪行为对自然人的侵害后果是由被害人或其家庭承担。因此,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追诉的愿望是最强烈的,也是最应当有发言权的,被害人的意志不应被全部被国家意志吸收,应当要尊重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主体地位。
4、刑事政策的要求,从历史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刑罚的适用与一个社会的发展的文明程度和执政治理理念息息相关。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发展和改革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司法追求的是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此外它与宽严相济政策所追求的社会效果相契合,在缓解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同时使失衡的社会关系重归和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社会发展和改革提供保障。
5、在国家主导下的刑事诉中,国家掌握刑事诉讼解决的一切权力,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被害人则成为工具性角色。这样的刑法模式不能很好处理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而会造成刑罚功能的日益低下。“在一个保护公民自由的法律价值体系内,法律应当确保公民在法律范围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判断行使自主决定权。”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分权从国家那里让渡一部分出来给被害人,让真正的受害者根据自己的受害程度在法律这个大前提下从被告人身上得到弥补,使其得到抚慰,确立被害人在案件解决中的主体地位。
6、法不外乎人情,法中有情,情中有法,同时法也离不开社会伦理。伦理和人情,是刑法适用时必须考虑的两个方面。社会伦理纲常是人民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方面的共识,在遇到分歧时是民众判断是非的准则,可以说被害人谅解就是法与纲常伦理很好的结合。将被害人谅解引进量刑,让人情伦理在纠纷解决中发挥其作用,对案件处理有很大意义的。
7、被害人实体利益受损的客观存在提出了现实需求,谅解的有效与否,直接体现了被害人可否对其实体利益进行自由处分。被害人谅解前提是被害人首先得有实质性的谅解权,这种权利的存在正是因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被害人谅解就是被害人是基于自己实体利益受损的事实,对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权利的自由处分。
五、完善被害人谅解适用具体办法和注意问题;
世界上没有哪种制度毫无瑕疵,刑事被害人谅解在适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我们必须完善其法律适用,使其更合理地影响量刑。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保证双方主体的自愿性,司法机关要注重这方面的审查。在恢复性司法的理念下,被害人利益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也有一定的决定权,被害人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谅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谅解协议的达成需要双方主体完全自愿,若非双方自愿,那么被害人谅解非但起不到修复作用,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增加诉讼累,即使是从宽也要宽之有度,滥用此项制度会适得其反。
为了更好地实施被害人谅解制度,要不断细化程序,完善法律法规,为双方当事人设立专门的和解环节,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和解事宜,并由司法机关和辩护律师参与到和解过程加以监督,约束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保证被害人谅解程序合法、合理、自愿且不违背公序良俗。
2、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被害人谅解应否作为量刑情节,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要参考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是否降低以及各种关系的全面系统的修复等。更重要的是要认真观察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反思罪行,建议看守所对每一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建立道德档案,对其日常行为表现记录在案,并兼顾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犯罪这两方面的要求,不能只看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谅解协议,就想当然地认为谅解真正达成,而草率地将该被害人谅解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一方面,坚决遏制和打击“花钱买减刑”之恶风,绝不能让群众认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保证那些经济能力不足却是真诚悔罪,且人身危险性减低、预防犯罪的必要性减低的犯罪人得到减刑。换句话说对于经济状况比较好的犯罪人可以加重被害人谅解所应付出的代价;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更多是要给予其必要的人文关怀,对于此类犯罪可以多一些人文关怀。一切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坚决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平性,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再是一句空话,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
3、避免刑罚不公,同案不同判。刑罚对每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公平的。横向上同罪,当同罚;纵向上,犯罪情节严重程度和犯罪后果应当和刑事处罚的处罚力度成一定的正比关系。被害人谅解对刑罚公平的冲击最大的是横向这方面的公平。被害人谅解也不可能是没有限度的,它的适用是有一定的范围,到底怎样惩罚犯罪人,被害人的意见跟想法我们必须听,但也不是被害人要求什么便是什么,被害人谅解在量刑时不能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另外,被害人谅解本来就是出自被害人跟被告人双方自愿,被告人能不能真诚悔过?要不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及其家属做出赔偿?被害人要不要接受被告人的赔偿?要不要就此原谅被告人?这些都应出自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任何人或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从中干涉。
结 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有理由相信,被害人谅解成为量刑情节具有一定合理性和合法性。然而司法适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说明现有规定是不完善的,还存在许多问题,在日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我们要不断完善此项制度,让群众既感受到法律的威严又感受到法律所蕴含的人性温暖,使被害人谅解成为缓和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好制度,体现其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L·阿克斯:《威慑理论》,雷丽清译.
[2]李宝忠:《刑法的价值体系及其取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3]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
[4]田宏杰:《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5]陈瑞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